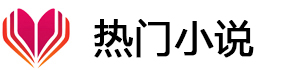卷末番外(2/6)
,他听见血顺着胳膊淌,滴在地面上,晕开一小片沫儿。这个地方他认识,打小就认识,因为班上自己喜欢的小女孩就住在这里,可“爹娘”和邻居们都说,这里百十来年都是魏家的粮食仓。
“我也不知道我跑什么。”
赵二官浑身都在颤抖,眼前一阵阵晕黑,可脑海里飘荡的不是对生的渴望,而是对死的疑惑。
“我在怕什么呢?”
他一直徘徊在废旧县衙门口,是因为一直有个问题想问问里面的鬼怪。
如果说人死变为鬼,那鬼就是“应该死却还没有真正死”;那如果是“还不应该活着却已经活着”的呢,也可以被称为鬼吗?
或许这世上,“鬼”从不是青面獠牙的模样,不过是存在的“错位”本身。
前者是“死的僭越”,后者是“生的早产”,本质上都是游离在预设的生死坐标之外的失重者。常人叫它们鬼,是为自己心里“该与不该”的执念,找一个能安放慌张的词罢了。
赵二官觉得自己也是如此,他像未到花期就破萼的芽,像未足月就落地的籽,带着“太早”的慌张,在“该生”的时刻表前,提前占了一个空位。
“糊涂着死,也好。”
一个影子往前走,手里的沉物举过头顶。赵二官闭上眼睛,听见风里的闷响,还有刃划破空气的轻响。他想起刚认识的小伙伴的眼睛,想起家里的锁门声,想起手上的血——要是能洗干净就好了,要是能刷刷牙就更好了。
影子走过来,用刃挑开他的衣襟,很快又收了刃。另一个影子确认了片刻,也收起了刃。两个影子转身走了,在夜色里越来越淡,像从没出现过。
赵二官背靠着一扇木门,头靠着柴扉,眼睛睁着。他攥着拳头,指甲嵌进掌心,血在地面上画了个小小的十字——像他平时洗手时,搓出的皂角泡沫印。
他最后听见了窃窃私语。
“……上头有令立即撤出,撤不走的悉数斩断……”
这一夜的崇安城,一边侧儿热闹非凡,一方却安静得死沉。城里人很快就会忘记,城里曾有一个六岁才搬过来的傻子。
这个傻子开始时也很聪明,就是每天守着些怪规矩,直至他在家门外茅厕,撞见一个被人淹死的浮沉女婴,被那张青紫色的脸吓得从此浑浑噩噩,便似乎再也没有长大过。
第二天巷口灯被重新挂上,新灯芯燃着,却照不亮青石板上的血痕,那道痕像条小蛇,爬过状元桥,爬过赵家门前,慢慢被后来的车轮碾得没了踪迹。
【番外二:外卖】
武夷山市的六七月,连风都是热的。
老农业局宿舍的老孙坐在客厅的藤椅上,老花镜滑到鼻尖,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戳了半天,才把“鱼香肉丝盖饭,多放饭”的订单确认提交。
空调遥控器就放在茶几上,他瞥了一眼,还是没碰——一度电六毛五,老伴旅游不在家,能省就省。
墙上的石英钟指向十二点十分,外卖还没到。老孙起身踱到阳台,往下看了眼楼门口那几棵老树,叶子蔫得打卷。
他自己的房子,早卖了给儿子付首付,这栋老农业局宿舍楼是老伴的,住了三十年,今年春天总算装了电梯,可装电梯那天,他跟三楼的邻居差点打起来。
按分摊方案,六楼要多掏四万八,老孙觉得不合理——“我爬了三十年楼梯,现在倒要多花钱给楼下的省力?”最后还是老伴偷偷转了钱,这事才算完。
打那以后,老孙更舍不得用电梯了,电梯门禁揣在裤兜里磨得发亮,他上下楼依旧是扶着楼梯扶手上上下下。好在他是当地